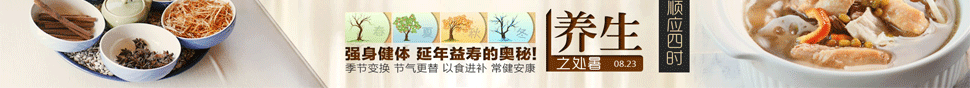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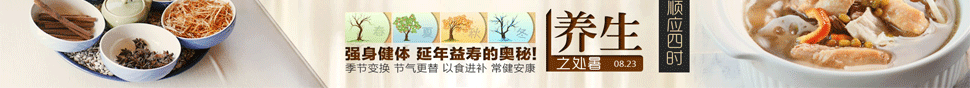
岁月的斑痕(十九)
文/姚水叶
秋雨无声润泥土,岁月无言报春晖。在极度缺吃短粮艰难度日的九月底,小芳没有盼回大芳的影子,放学后独自一人在收过萝卜的泥土中寻找核桃粗的、拇指粗的小萝卜,在柿树上寻找给麻雀留的软柿子,寻找即将枯萎的野菜。提起战地的名字就让双手打哆嗦的小芳她妈,做的苞谷糁浮起了筷子,程有良知道前半年的米面大多都进了战地的嘴,后半年只能凑合着过了,但小花花太小,他思量了多日,终于下了决心,对小芳嘱咐道:“小芳,到礼拜天把花花给你姐送去,这都几个月了,顺便看看你姐过得咋样,看棚漏雨不,让你哥弄些稻草把漏雨的地方盖扎实。”
“爸,我不认识路咋送?”
“唉!说到底还是女娃太懦弱,现在的社会也好,米里生,面里长,我这一代人像你这么大都扛起枪走千里路了,你现在能做啥?把娃背上,嘴学乖些,叫叔叫婶边走边问么!”
小芳她妈说道:“自从接了亲都几年了,以前咱不去能说得过去,现在大芳跟战地回去了,你不亲自去一回像个啥,我那时刚嫁进咱屋,逢年过节盼你去我娘家给我撑面子,盼我爸来也有娘家,我爸却认为我嫁给你不用他操心,脚印从不踏进咱的门,直到六三年我爸死了也没来几回。咱俩对大芳亏欠得太多,娃不说,咱要知道,你送花花也是个机会,叫他屋人也知道咱娃有娘家呢,不是舍给他屋了,时间舍一天就是少挣十分工,也不算啥,以前穷人把娃给婆家,他爸不放心,半夜扒在烟囱根摸墙皮,看娃睡的是热炕还是凉炕,再从烟囱冒烟口往里塞些柴禾,都不敢叫婆家知道,尽管不顶用,但娘家把心尽到了,今也不用你拿柴禾,去看一回。”
程有良听完老婆的话心悦诚服地嗯了一声,对小芳说道:“你就不去了,爸去,去看看你姐!”
第二天小芳她妈做早饭时,把攒了好长时间的六个鸡蛋煮熟,对程有良说道:“天冷了,鸡很少下蛋,你把这几个鸡蛋装兜里,战地说回去每顿都炒一碗鸡蛋吃哩,我估计他还没鸡蛋炒,把这鸡蛋给战地两个,给大芳两个,你走饿了再吃两个。”
程有良立刻剥了一个鸡蛋喂给了小花花,他自己也没舍得咬一口鸡蛋,并对花花说道:“快入冬了,鸡也不下蛋了,爷今年挣得少,养不活你了,爷听你奶一回话,送你回你屋。”
自从战地前几个月用生产队的架子车接回大芳后,见了乡党就给乡党介绍大芳:“婶,这是我女子她妈大芳。”
又对大芳说道:“大芳,快叫婶,这是门楼梅利婶。”
大芳看着梅利婶和自己差不多大,便知道人家的辈分高,就显得很客气地叫一声:“婶,你来了,快坐!”
梅利笑哈哈地说道:“怂战地,我比你小,以后甭叫婶了。”
战地连忙咧着嘴笑道:“你人碎辈分高,我还有不叫之理。”
梅利又对大芳说道:“甭听他的话,咱俩是乡党,娘家离得很近,我知道你,你没见过我,以后我串你门,你也常串我门,缺啥少啥尽管吱声,只要我有就给你。”
在大芳的心里,这是最亲近的一刻,也是最激动的一刻,更是在自己面前敢叫自己串她屋门的人,相比之下,在娘家从小到大都没有串过门,串门对她来说是奢侈的愿望,二十多年的岁月里,除了乡党偶尔借东西时和她才有答言的机会,没人借东西时她便是香炉里的灰,她也很希望乡党去借东西,可三间房里空荡荡的,自家有的,人家也有,自家没有的人家还有,所以,一年到头屋里也见不了几个乡党。回到这不一样,尽管乡党都是带着好奇的眼光来看她,也让她激动不已。她站在两间草棚的屋外,看到了大村的人,看到了山外的世界,故北村人居住集中,几乎墙东墙西,房前屋后都是几家几十家,不像上坡村人居住分散,除了分粮、开会能见到人,平时很少见乡党,这里隔条小巷就是二队,过条丁字路就是四队。稀奇的她出了门见谁都叫,不论穿戴阔绰还是衣衫褴褛,在她眼里都是伯,都是婶。从半生不熟的上坡村回到知根知底的故北村,战地的心更有了归属感,谁家有需要他出力的事,他都从不推辞,前声叫,后音到。大河涨水时,康学叔在河里发现一棵被洪水决断根,剥光皮的白杨树,个子矮小的他费尽力气截成两截,还是拉不出河岸,脑海里闪过了一个个乡党的模样,最终还是选择了好说话的战地,他抱着碰碰运气的希望找到战地,哆哆嗦嗦地掏出一根纸烟,递给战地并用央求的口气对战地说道:“叔在大河里捞了两截木头,想寻人帮忙放到架子车上,问了要过桥的几个人,都说不行,你去看能帮叔的忙,叔给你一截木头成不?”
战地慷慨地问道:“叔,架子车在哪?”
“架子车在河边!”
“走么,我给你帮忙,不要木头。”
走到河边,战地、康学叔拿来的麻绳拴住了带有树杈的地方,说道:“叔,我拉你拽!”
但康学叔的手臂使不上劲,木头在水里纹丝不动,他俩又调换了位置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木头离水。战地又铆足了劲,用力抱住木头的一头,大声叫道:“叔,赶紧把车辕往木头底下塞。”
康学叔得到了战地的帮助,又一块拉到门前小路口,对战地说道:“你歇息一会,我再叫俩人一块抬。”
二十分钟后,康学叔求来两个人,对那两个乡党说道:“咱走战地那,战地可能在他屋等咱几个呢。”
几个人站在战地门前喊道:“战地,战地!”
只见战地端着饭碗应道:“哎!叔,你回去,两截木头我全给你扛到后院了,前院没地方!”
由于战地帮了谁都不愿意帮的忙,更让三队社员对他刮目相看了。从此,战地的草棚屋成了故北村三队乡党乐意串门的地方,老实巴交的公公婆婆也成了饭点的常客。蔡金秀端着饭碗从北逛到南,进了大芳的门,很不服气地说道:“大芳,世上有两种人,一种是一勺一碗的实诚人,一种是鸡蛋掉在油瓮里用擀杖捞的奸滑人,有用的你叫她来,没用的就不要叫,不见得谁都是好人,早知道有这两间棚,我都住这了,都怪康怀叔,没经过战怀,自作主张把战地安排到这了,他妈他爸吃碗饭还得走几个巷子。”
听了嫂子的话,大芳口头嗯了一声,但她还是她,该称呼的乡党一个也不能少,她跟嫂子不一样,求人的时候多,于其临时抱佛脚,不如平时多烧香,人气都是攒的,何况妈妈也常念叨“有今世的公婆,没有来世的公婆”,他们再邋遢,也把战地养大了,还比自己强,生了仨儿子,自己还没生一个儿子呢。快入冬了,大芳望着露水打湿的柴禾堆,更希望花花回来,更希望草棚里能有爸爸和妹妹的身影。
程有良背着小花花来了,战地高兴地从丈爸的背上接住了小花花,告诉大芳:“给咱爸做纯米饭,不要放萝卜丝!”
大芳知道,他们回来挣的工分太少,分的口粮也不多,分的萝卜不少,早上是苞谷糁萝卜条饭,午饭是一碗大米,一个几斤重的大萝卜,先把萝卜丝焯熟,再另外添水倒入大米,等熬熟到九成,给小女儿撇出一小盆米饭汤,然后和萝卜丝拌匀蒸熟,再匀出一小盆米饭,等晚饭时再加一个小萝卜,那一小盆米饭汤也足够让小女儿喝几顿,这样就能节省更多的大米、苞谷糁。大芳没听战地的话,只是多加了少半碗大米,仍然和以往的做法一样,让远路而来的爸爸吃了一顿和以往不同的大米饭。趁大芳做饭的时间,战地领着丈爸在生他养他的粮田边转了一圈,从丈爸的表情里透出了对一眼望不尽的大块麦田、稻田的热爱和羡慕。程有良临走时,战地悄悄地从炕角的炕席下取出了粘在炕席背面的两毛钱,给小布袋里舀了三碗大米,装了两个最大的萝卜,对程有良说道:“爸,这是两毛钱,出了村有通往去咱公社的公共车,走路太远,您坐车回去。”
程有良坚决不要,反复说道:“屋里啥都有,我比你宽裕,不要钱,走路畅快,只要你过得好,我黑了睡觉踏实,花花回来了,多张嘴哩。”
程有良看女儿的消息沸腾了故北村,凡见到战地丈爸的少数人都相互传言:“好人,不是一家人,不进一家门。”
返程的路上,程有良反复思量战地不该倒插门,不该在自己家里白熬两年。那天晚上,程有良真正睡了一个安稳觉,连呼出的气都是宽心祥和的。
姚水叶(女),陕西西安人,于一九七八年毕业于太乙宫中学,以耕农、养殖为生,更爱文学,喜欢用笔写方式向读者传递善良,传递亲身体会过的人间美德,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,对生活抱以崇高的向往。